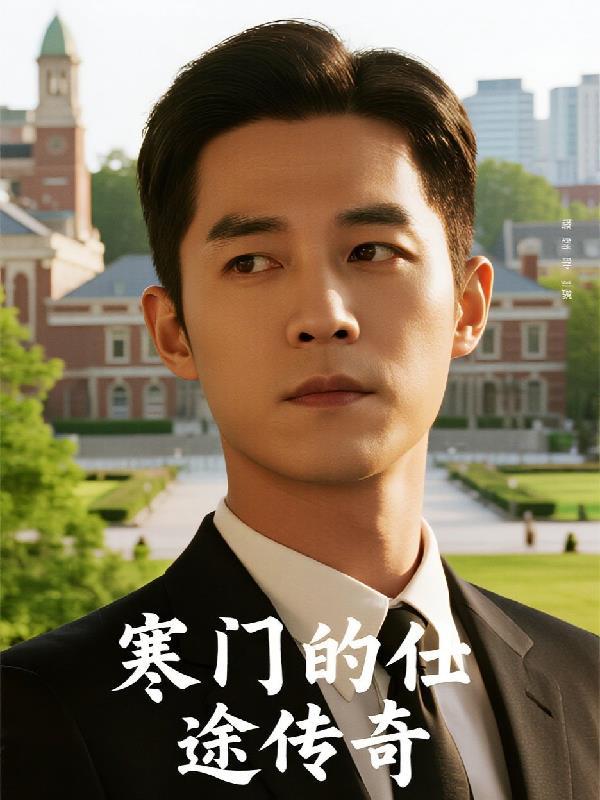书籍简介
首章试读
楔子 1977年的关中平原,秋风裹着黄土掠过田埂,把秦家院角的老槐树叶子吹得簌簌落。14岁的秦宇轩蹲在树下,后背垫着捆晒干的玉米秆,手里捧着本封面磨白的《高中语文》,鼻尖几乎要碰到纸页——这是村小学张老师退休时送他的,书页间还夹着张泛黄的纸条,写着“宇轩聪慧,当惜才”。 这话他记了三年。五年级那年,张老师带了本《新华字典》来上课,秦宇轩凑在讲台边看了一眼,就再也挪不开脚步。软磨硬泡借到字典后,他把这本“宝贝”揣在怀里,白天跟着父亲去地里拔草,歇晌时就坐在田埂上翻;晚上凑着煤油灯,趴在炕桌一角逐字记,连吃饭时都在嘴里默念“b-o-波,波浪的波”。四个月过去,他竟真把整本字典“啃”了下来——张老师随便指个“龃龉”“耄耋”,他不仅能念出音、讲清意,连在第几页第几行都记得丝毫不差。从那以后,“秦家小儿子是个读书料”的话,就在村里传开了。 “宇轩,给你爹端碗米汤来!”屋里传来母亲张卉玲的声音,带着点刚蒸完馍的热气。秦宇轩应着起身,合上书往屋里走,就见父亲秦天月,小名秦老实,因为很少说话,大家都习惯叫他秦老实,此时正坐在炕沿上,正用巴掌轻轻捶着后腰,眉头皱成个“川”字。父亲的腰是前两月伤的——那会儿为了多赚点钱,去县城火车站当搬运工,扛着半人高的“货包子”(搬运工对货物包的俗称)走站台,没留神脚下的坑,猛地闪了腰。没钱去大医院治,就找村里郎中贴了两贴膏药,至今未好,重活暂时也不敢干,只能帮着家里喂喂猪、拾掇拾掇菜园,却总说“能多干一点,娃们就少受点罪”。 “爹,我给你揉揉。”秦宇轩把碗递过去,伸手替父亲按揉后腰,指尖触到发硬的肌肉,心里像被针扎了下。父亲喝了口米汤,摆了摆手:“不用,老毛病了。你快看书去,别耽误了。” 这时,张卉玲端着盘蒸红薯走进来,把最大的一个塞到秦宇轩手里:“快吃,是姐特意给你留的。”秦宇轩捏着温热的红薯,鼻尖一酸,大姐秦萱荣22岁,上完了初中,原本能接着读,却在毕业那年主动辍了学,跟着奶奶学纺线,一边上工一边纺线,说“把钱留着给弟妹买书”;二姐秦萱芝21岁、三姐秦萱慧19岁只上完小学...